
報道:胡清心
移民潮開始不久,專業人士、白領、碩士畢業生都在工廠「pack gingerman」,幾乎成為一種都市傳說,確實大量港人移英之後,都選擇告別在港的白領職涯,而以藍領基層工作維生,甚至衍生出專為港人移民介紹工廠或貨倉散工的仲介產業。華人自古信奉「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」,從坐辦公室到從事體力勞動,定然是個不容易的轉變,心態衝擊可想而知。
在香港,牧師、傳道人,雖然未必高薪,但也是受人尊重的職業。然而,不少牧師、傳道人移民之後,與他們牧養的群體一樣,也成了倉工、搬運工等等勞動力大軍中的一員。然而,身份轉變,不代表信仰思考和受召之心的轉變,本專題訪問四位前傳道人,他們有的失業、有的「還俗」、有的在養家糊口之餘仍盡力牧養群體,但相同的是,當轉變的處境與既有信仰發生衝突的時候,他們都沒有放棄在懷疑中思考。面對從未預想過的困難、衝擊和挑戰,有的人似乎還在隧道中摸索,有的人似乎已經看到了新的神學的模樣⋯⋯
王礽福:「見好就收」的牧職觀
宣道出版社前社長王礽福是早期離開香港的教牧之一,這無疑與他在反修例運動中的高調言行不無關係,2020年7月1日《港區國安法》通過,隨即王礽福便成了大公報和文匯報的攻擊目標。儘管最初王礽福去意並不大,但隨著形勢愈發嚴峻:WhatsApp被入侵、開始遭人監視、收到離開香港的勸告⋯⋯加之家人無法接受他坐監的可能,慢慢決定並開始著手準備離開香港。「台灣是我的精神故鄉,所以一直想退休之後在台灣生活,(在那裡)已經買了樓」,最初王礽福考慮移民台灣,並於2021年1月落腳,並和王少勇共同成立淡水香港教會。不過考慮到孩子的教育問題,太太又有BNO簽證,他最終還是將英國作為了紮根之處。原本打算台灣、英國兩地跑,哪曉得持有BNO簽證需要「坐移民監」,於是便只能一心待在英國。2020年10月,王礽福有份成立的榮光敬拜事工宣布停止運作,「大家覺得見好就收。離開的時候也明白,離開愈久,和香港之間有隔閡,雖然資訊流通,但如果你人不在其中,怎麼都是隔了一層。」就此,王礽福彷彿給過去的牧職畫上了一個休止符,開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體驗。
在香港幾乎一生都在教會或者機構中工作,在台灣也一直經營線上和線下的牧養工作,王礽福可算是資深教牧同工,自然覺得,到了英國或許能在港人信仰群體中延續自己的工作。然而沒想到的是,來到英國已經一年多,卻鮮有教會邀請王礽福主日講道,更遑論在教會擔任牧職。對此王礽福倒是很坦然,「祭司都有退休年齡,我見過太多退而不休的牧師。你很想事奉,但未必他人喜歡你的事奉。一些老牧師可能年輕時候講道很好,但講道風格會過時,而自己也會退步,適時退休也是好事」。他並不惦記19年時自己站在歷史聚焦點上的光芒,「我覺得只是那麼巧,當時我在不同機構組織中,都有不少職位,我講的話中聯辦很關心,而你在那個位置上,就應該講應該說的話,這個使命我做到了;但如果沒有這樣的位置,我可以提早退休,何嘗不是上帝給我的福氣呢?」他只是覺得當下處境並沒有繼續在教會服侍的機遇,那麼便「見好就收」,他形容不要把人生「從正數變成負數」,「慢慢過氣而不自知,(希望)人生結束的時候還處於正數。」

信仰珍貴之處,是上帝對受苦者的肯定
沒有牧職仍要養家,2023年開始,王礽福嘗試過不同的基層工作以謀生,包括在香港超市做兼職店員,並在晚上做兩小時清潔,「當然包括洗廁所,我不覺得是絕對接受(基層工作)或者絕對不接受,當然你在舖頭有人叫你王社長,還是會有點尷尬,但我覺得這大致是少數情況。」問及為何如此坦然,他表示和自己是從「異教徒」成為基督徒有關,雖然自小信主,但以往常常和自己的嫲嫲返佛堂,因此看過一些佛學書籍,他形容自己有少少慧根,也種下了他對人生態度的種子:人生如苦海。所以王礽福說自己信教的原因並非成功神學或者幸福神學,從鄙夷基督教到信主,轉變發生在他中三、中四時期的一個佈道會,佈道員提及哀慟的人有福了,這讓他意識到「原來這個上帝不是膚淺的,人對人的那種哀慟,原來他會在意,更會安慰那些哀慟的人。這個位讓我覺得信仰是真實的。」
對王礽福來說,人生的艱難是非常實存的。人有順境,比如他曾擔任宗派副主席、出版社社長和兩個聯合組織的主席,「某程度會覺得人生就差不多到這個位置了。」突然變成一個兼職店員和清潔工,他並不覺得很難適應,對於這種轉變更是豁達。「你當初坐這個位置,是因為你很厲害嗎?不是,我做社長也不是很稱職」,因此失去這些也不覺得遺憾,相反基層勞工自有其快樂的地方,「做清潔的時候,還可以聽有聲書,我很享受這個過程,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東西。」中文系畢業的他,自認有一份愛讀書的底子,以往因為機構工作繁忙,沒甚麼機會讀書,現在則可以大快朵頤。他笑言,在香港,教會工作是一份厭惡性工作,那時他常常想要辭職,反而現在做基層勞工,雖然生活不富裕,但「自己本身就是基層出身」,如今返回基層勞工的崗位,並不覺得可恥,更不感厭惡。
談到這裡,必然會提及這段嶄新的工作經驗,有沒有令王礽福對香港教會長久以來關注的職場神學有新的看法。他表示香港慣常講的職場神學,多是如何在職場上見證上主,「撈得起」,但英國社會在這方面心態很不同,關乎的是整個社會的大環境。「真正的職場神學,要創造一種讓人覺得做基層都很有尊嚴(的生態)」,他提及在英國最低工資著重的不是一個具體的時薪,而是即便賺的是最低工資,勞動者一樣也足以養活一家人,所謂白領和基層的工資差別並不大,足以影響社會整體的氣氛,因此在教會中也感受不到階級差別,更不需要標榜自己的職業和身份,「你想在香港教會(信徒)幾緊張要別人知道自己係咩身份」。這也讓他對福音書中,拉撒路和亞伯拉罕的比喻有了新的看法。「大家都在想這個財主做了甚麼壞事,(但這個)故事你不覺得他有多壞⋯⋯不是大奸大惡。這個故事(其實)說的是,就算我的人生進入下行之詩,最差做了乞丐,但在基督信仰中,做乞丐的,也是在亞伯拉罕的懷中⋯⋯這是信仰的顛覆性,不斷提醒我們,不要在世界中或者既有架構中,尋找你覺得很重要的。這個故事安慰我們的是,無論你的人生糟糕到甚麼程度,你都在上帝的懷中。」正如馬太福音中的「八福」所描述的,都是很糟糕的境地,「我們對福的定義,是順境,很物質的東西」,但聖經教導的,是對如何待人處事、對正義的追求,這些追求本身就是一種福份。王礽福再次提及自己歸信基督教的原因,「基督教可貴的東西,是在悲苦人間裡面,上帝對受苦者的肯定⋯⋯很多人一生都是勞苦,但也有盼望最後可以是在亞伯拉罕懷中的拉撒路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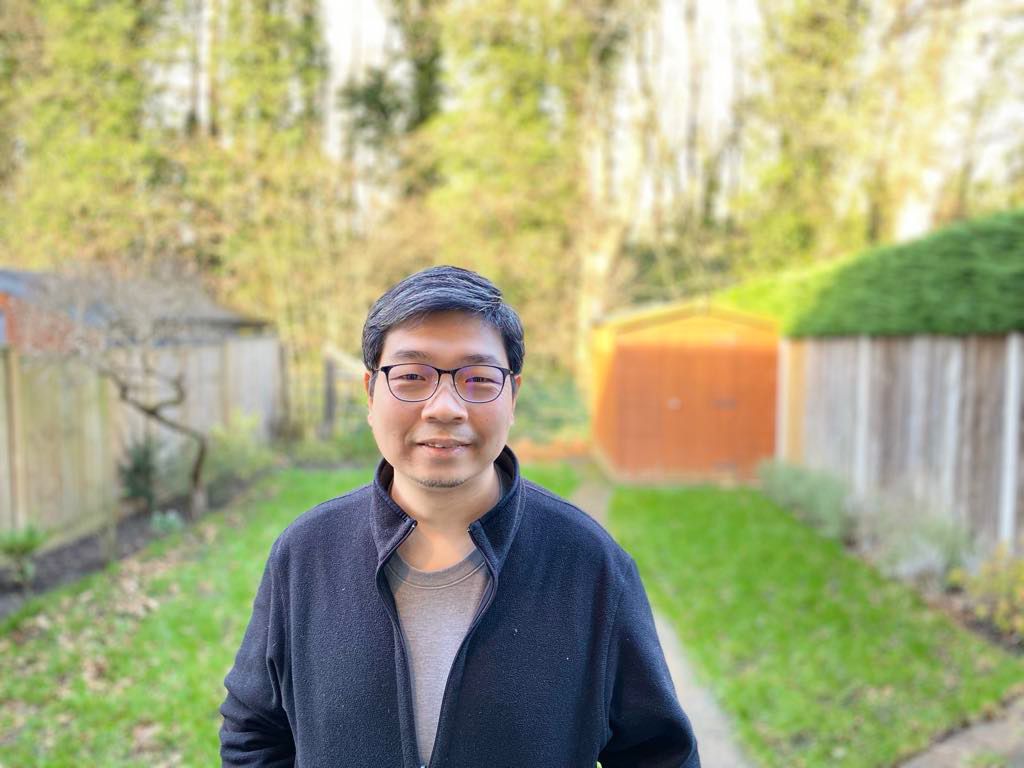
洗淨鉛華,儒釋道是他心境坦然鬆弛的資源
不僅是自己的生活,對王礽福來說,19年後整個香港都處於一種瓦解的狀態,再也沒有甚麼是理所當然,曾經安逸而簡單的對世界和生命的詮釋已經行不通,而這在他看來,正是「神學的黃金時代」。「留在香港的人,你如何去教導信徒,甚麼是真實和公義⋯⋯我們如何用天啟的語言,重新向弟兄姊妹講述信仰,讓他們心領神會,這是很大的挑戰」。而同時,離開香港的異地生活,也會讓人發現,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對生命的詮釋,在這裡卻行不通,「現在我們要反省過去的香港經驗,有些東西只不過是歷史碰撞下的偶然機遇,所以你覺得理所當然,但當你離開了,發現這些東西行不通,你才會更清楚信仰是怎麼一回事。」儘管不再牧會,王礽福形容自己的信仰思考仍很豐富,包括如何處理自我。「我覺得忘我很重要,太看重自己、自卑自大等等,是我們要處理的。」
無論留港還是離港,何為香港人,何為香港精神,都是一眾學者、文人或者傳媒人,孜孜不倦究極探討的話題。喜愛讀書的王礽福的詮釋別有一層浪漫的色彩:「我會將現在的香港想像成49年之後的上海,現在所謂香港情懷的電影,都是七十年代、八九十年代的香港,所謂的香港已經是一個過去式」,正如人們說起老上海,指的是49年之前的上海,而在49年之後再無人能代表上海。他更提及49年後上海移民與香港之間的關係,「老上海是隨著(上海移民)在香港復活,成了2.0版本,又變成了香港人,加入其他族群中」。或許某種程度上,可以承認曾經的香港已經消亡,但王礽福認為消亡並不代表死亡,正如老上海的十里洋場已經逝去,但作為文化符號仍迸發出多種多樣的文創作品。
「我作為讀文學的人,很喜歡民國上海,燈紅酒綠的糜爛裡面有一種美好,正如八十年代的香港,有九龍寨城、梅艷芳,也是糜爛的,但我們很眷戀那個香港,就好像耶利米哀歌不只是在哀嘆,也有對糜爛的眷戀,糜爛中有美好的東西,其實已經有能力成為一種文化資源。」王礽福以文藝復興和唐宋八大家為例,指出復古也可以是一種創新,「對過去香港的回憶和反省可以創造新的東西」,重點是如何善用這個文化資源,就好像老上海來到香港成了上海2.0,但又不完全是上海2.0,也成了香港1.0。
這數年從香港來到台灣,最終在英國落腳,無論個體還是整個共同體,都經歷數十年不遇之大變局,王礽福也同意,這幾年的風雨於他而言,猶如洗淨鉛華,當信仰外在的東西被洗去,自要思考甚麼是信仰的核心。但他並沒有因此對信仰產生質疑,卻有了更多的肯定。「在我裡面有一種儒釋道的東西,它能幫助去面對這種環境的轉變」,這讓他重新肯定公義與愛的重要,還有「人生可以在下行狀態唱上行之詩」。當失去的太多,王礽福才更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東西是甚麼——讀書,「我喜歡讀書,現在做基層勞工,所有外在名譽地位都沒有了,我還是喜歡讀書」。
蝸居於英倫小鎮、從事基層勞工工作,再無繁忙的講道教務行程,也沒有一連串的頭銜與職務,王礽福卻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加有福,因為信仰的盼望是真實的,「個人可以面對到帝國,在巴比倫羅馬帝國之下,不是按照他們的價值生活,對世界有另一種詮釋系統,眼前未必成功,永恆中卻可以存在,可以令人心安。」
Vivian & Joe:雙雙失業一年半的艱難移民路
Vivian和Joe如同很多雙雙在教會事奉的夫妻一樣,過往十數年,出入於不同堂會的幹事崗位上,二人為減輕經濟負擔而設定了進修神學的時間表,Vivian於十一年前神學畢業,而Joe則等到家庭穩定之後,於19年入讀神學院。如果不是因為移民潮,可以想像得到兩人和他們的孩子們未來的生活軌跡,便是在家庭與教會之間遊走。
最初移民的決定是Vivian提出的,受其母親和妹妹移民影響,她想不如全家一同移居英國,原本打算籌備一兩年再出發,但由於不想讓孩子打疫苗,加之彼時在幼稚園擔任宗教老師的Vivian已直觀地感受到社會中言論自由和政治氛圍日趨收緊,因此當機立斷,匆匆於2022年底移民英國。
受訪之時,已是2024年的8月,這一年多來,Vivian一直處於失業狀態。她並非對新生活沒有憧憬,但求職屢屢碰壁,「傳道人」這個工作經驗在英國死板的招聘流程中毫無意義,「他們都是用AI篩選你以往的工作經驗⋯⋯香港的傳道工作經驗,無法讓AI有理據相信你會做一些文件工作,會用電腦」;另一方面,抵英之後不多久,她便發現自己意外懷孕,為了照顧新生兒,她也無法工作。
當下,Vivian唯一能賺取收入的方式,是做一些手作在網上售賣,她形容自己如今如同保羅一樣,「織帳篷為生」,在過去她並不認同這種傳教方式,直到在香港時,從教會崗位轉職到幼稚園宗教老師,Vivian逐漸感受到,離開堂會的框框,反倒多了許多與同事家長分享信仰的機會,更體會到保羅的那種自由。或許因此,她能更坦然地接受當下的非傳道人身份,「我還可以找到牧養其他人的機會,不是牧會,而是牧人。」她考慮過在本地結識一些家庭,利用英國居住空間寬敞些的優勢,與丈夫一起做夫妻牧養,舉行家庭聚會。然而,對此她的丈夫Joe卻坦言「未Ready」。

採訪之初,Joe便提議夫妻二人分別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,因為兩者並不相近。Joe神學畢業正撞上移民潮,外母又提議全家移民,「當時我是拒絕的」。那時他的使命責任,是做年輕人的牧者,「(我接觸的一些年輕人)本性是純良的,是乖的,都是為伸張正義⋯⋯(我思考的是)如何既可以伸張正義,但同時不違背耶穌的教導呢?」畢業後,Joe參與服侍的教會正逢年輕人斷層,「我希望復興年輕人」,那段時間,他形容自己很開心,感到做著有意義的事情。「我想我幸運的是,我能夠在崗位上做到我事奉想做的事,不需要被要求做甚麼,做一些不務正業的工作。」
儘管家庭有移民打算,但應聘這份工作的時候,Joe和Vivian都以為移民至少都是兩三年之後的事,因此Joe還有足夠的時間委身於當下的教會。沒想到做了大半年,Vivian突然改變計畫,「要即刻走」,對於Joe來說只感到無奈,「一次在職事會講了(移民)這件事出來,我忍不住哭了出來」。儘管試過不同方法,讓太太一家先行移民,他則拖延離港時間,也只是權宜之計,終於都在22年11月底與家人在英國匯合。
「當我知道確定要離開的時候,我已經很清楚一件事,我很難找回牧職的工作」,Joe現實地說。一來,當地華人教會數量有限,未必有職位空缺;二來,自己的英文能力未必能在全英文環境中做牧養,加之初來乍到,不熟悉當地文化處境,更難在本地人教會中服侍。缺乏牧養群體或對象,自覺擅長貼身教導的Joe不由感到迷茫,也曾嘗試透過網絡繼續服侍教導原本離職的教會,包括開網絡聖經班等等,但時差與時間造成的距離,終究使兩者漸行漸遠,「會有一些人走茶涼的感覺」,這也讓他意識到,「決定走這一步的時候,等同於say goodbye」,這都是他未曾預料到的,更影響到他對信仰或神學產生懷疑。
「這個上帝係咪好雜」?
動搖他原本信仰或神學信念的,並不只是牧職上的茫然,也源於生活中的孤獨和挫敗。「我本身在香港的時候有很多朋友⋯⋯只有我一個決定移民⋯⋯我覺得很孤伶伶」,在香港每週三晚會與朋友一起打乒乓球的運動,也沒法繼續。沒有車牌,出入不便,自然找不到工作,至今只短暫做過幾份散工;小朋友返學只能趕巴士,假日也難照顧小朋友,帶他們外出遊玩⋯⋯「我有種感覺,我在這裡做甚麼⋯⋯開頭覺得是否因為我離棄上帝的呼召⋯⋯所以上帝掩面不顧我?開始會懷疑上帝,你是否真實的呢?或者我不覺得你是假的,但其實你都有限度?」或許是自己的現實困境太渺小,但環視周遭正發生更嚴重殘酷的戰爭與衝突,「上帝也沒有出手,上帝是否沉默呢?」Joe每晚都會和兒子一同睡前祈禱,但面對兒子他都忍不住道出自己的懷疑:究竟這個上帝係咪好雜的?
除了信仰震盪帶來的深深懷疑,Joe感到從現實角度來看,當下也不宜組織家庭聚會。「(剛移民)計畫未有最小的朋友,太太英文好一點,又有碩士學歷,可以出去找全職工作,我照顧小朋友,但現在因為有bb,很痴媽媽,成為阻礙我們找工作和經濟收入的障礙,這樣的情況底下,已經耗盡我們的心力。」
尚未在異地安居立業,仍為日日柴米油鹽發愁,風雨飄搖中的小家,又遇上計畫之外的新生命,Vivian和Joe都坦言,雖然不曾想過墮胎,但都感到這個小生命來的不是時候。「困難已經夠多,還要加多一重困難,這個耶和華所賜的產業究竟是祝福還是詛咒?」Joe打從心底裡有所質問。Vivian亦表示,接受現實和這個新生命之外,已經沒有心力「去想其他包裝的說話」。
丈夫對信仰的灰心喪氣,更影響到了兒子,「他也會說爸爸是相信(上帝的),但現在不信」,Vivian亦坦言很難維持家庭的屬靈氣氛,沒有車週日難返教會,更難做家庭崇拜,現實更難以見證上帝是聽祈禱的。「一開始還堅持和小朋友(祈禱),現在都不知道祈禱甚麼了,講了十天、兩個月,希望明天能找到工作,還是這一句,如何跟兒子交代?」
雖然仍努力對未來和上帝有所盼望和希冀,但Vivian也有懷疑信仰的時候,「人始終需要安全感,以前在香港生活是很踏實的,但現在生活中突然沒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,又發現信仰好像未能給你提供支援」,她形容自己還在摸索中,可是還沒有看到隧道的出口,似乎困住了。「我以前在香港牧會,對著基層的弟兄姊妹,會跟他們說,是啊,這個苦難不會走的,但上帝會陪著你。但我自己現在在苦難中,才發現這句話對自己說的話,其實都挺難聽,我自己都覺得難信,上帝現在還陪著我嗎?」
樹牧:駕巴士的義務傳道人
樹牧(化名)目前在伯明罕牧養著一間自己成立的港人教會,但在平日,他的身份是當地的巴士司機,每週返三日工。抵英三年,在找工作這件事上,樹牧有自己的節奏,「(一開始)當然人生地不熟,所以休息了三個月⋯⋯剛剛來到還有一些積蓄,因此不急於找全職工作,想樣樣東西都試一下。」他做過教學助理、裝修,做過最長的一份,是在倉庫工作,同時在當地華人教會服事,並於2022年7月開始建立新的教會。
「積蓄用到七七八八,就要找一份比較長遠的工作」,雖然心繫教會,但樹牧坦言當下教會的經濟能力,尚不足以聘請一個牧者,短期內他不會指望透過牧會養活全家,既然如此,就考慮「有甚麼工作我不太討厭」,自覺最能駕馭的工作,是駕巴士。

既然牧會無薪,更要為謀生而駕巴士,何不考慮放下牧會,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產出收入的工作上呢?樹牧表示,一方面是因為「某程度上都有一團火」,在港事奉九年,他一直都是在學校牧養學生,「我很喜歡做,事奉喜樂的狀態多過不開心」,對牧職仍有熱情;其次想體驗在教會牧會與過往在學校牧會有何不同;加上眼見當地港人的需求,便決定不計回報地瞓身投入。
「教會經濟學」注定港英教會生態大不同
雖然在英牧會日子不算太長,樹牧已經敏銳地觀察到港英教會生態大相徑庭,而這和兩地的地理、經濟及社會因素分不開。在香港,教會生活往往佔據了信徒生活的大部份時間,相應教牧亦相當忙碌,週間晚上有團契和小組,週末亦然,充實的教會活動塞滿整天的行程,從早到晚年中無休。然而在英國,教會生活可能只限於週日上午,主日崇拜結束,會眾便「做鳥獸散」。
樹牧認為,香港的優勢是地理空間小、交通方便,「平日叫弟兄姊妹返教會都不困難」,而信徒多中產,所以閒暇時間有更多知性層面的追求,需要教會滿足。但是英國地廣人稀,「(來到教會),駕車可能有半小時車程,如果搭公車,就要一個半小時」,因此交通和時間成本都太高昂。另一個更主要的問題是,在英國「沒有工人」,夫妻雙方不能像在香港時,把小孩留給工人照顧,全情投入各式各樣的教會活動。
「我們教會的模式,是週日有兒童崇拜、成人崇拜和青年崇拜,都在十點至十二點之間舉行,沒有任何其他活動,除了加插主日學,都但很短暫。」如此從簡並非是想偷懶,而是照顧會友全家「同出同入」的需要:「如果來教會,有些家庭只有一輛車,一旦出動就是所有人都要一同去,所以沒有可能讓他們分散活動」。至於以往一些香港教會把週日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的作法,在這裡一樣行不通,「以前能夠那麼做,是因為家裡有工人幫你煮飯,打理家務,這裡你回到家還要買餸煮飯,要預備星期一小朋友返學」,因此主日崇拜只能「一切從簡」。卻讓樹牧更反思對於教會來說,最重要的是甚麼,「當在這個生活狀態下,最重要的,是一個信仰基督的群體,定時定候在地上敬拜上帝,這才是教會最核心的一件事」。
雖然在香港服事多年,但要說牧會,甚至是創立教會,樹牧仍算是新手,而他也感到,在英國的經歷讓他大開眼界,甚至直言曾經的自己簡直是「井底之蛙」:「香港開埠已經有百多年歷史,很恩寵地因為歷史因素,有很多教會經營、神學院聚集在香港,讓你習慣了以為教會必然如此⋯⋯你不用想申請88牌,如何建立教會會章,不用想教會財政,青蔥傳道人剛入職,你只需要牧養群體,基本工作有幹事負責,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制度」。但在英國創會,一切從零開始,而最大的衝擊便是沒有錢,不僅教會沒有錢,他更驚覺,與香港不同,在英國做傳道人就是一份沒有錢的工作。
樹牧表示,這種分別牽涉到港英兩地不同的「教會經濟學」。在香港,教會信徒普遍收入都偏中產上下水準,奉獻也穩定,三百人的教會就請得起十個同工,甚至誇張一些,有些教會只有二十多個會友,也能負擔得起兩個傳道人和一個福音幹事。「現實點說,在香港你會看到教牧算是一個有規模的職場,人工不算高,也不算低,當這個職場生態不斷轉動的時候,可以推陳出新,不斷有年輕人加入,某程度上,這也是一個可以存活甚至做到退休的職涯」。
但在英國,樹牧以伯明罕另一間有約三百會友的港人移民教會為例,會友奉獻所能支付的,只有一個兼職傳道人的薪金。這離不開當地的移民生態,「新移民教會很多都是退休人士,沒有收入便沒有奉獻;有些是半退休狀態,就算有工作也不會很積極爭取上游,只是求個安心,奉獻也不會多;有些可能積極工作,但畢竟不是多數。」而英國藍領白領人工差距不大,收入水平較平均,專業人士也未必有高薪,自然奉獻也不多。「以前在香港整天說,歐洲教會衰落沒有傳道人,到這裡就明白,不是沒有傳道人,不是沒人願意做,是教會沒有錢請。」樹牧分享,連英國本地教會大多都沒有聘請全職傳道人,甚至有些義務傳道要照顧幾間教會,這讓他意識到原來香港教會的豐盛,在普世教會中,是一個異數。
為甚麼在英港人甘做藍領?
港人多有本科以上學歷,離港前往往從事體面的白領工作,為何來到英國甘願做藍領,做工廠工人、貨倉甚至清潔,為何不發揮一下「獅子山下」精神,透過進修晉升回歸銜接以往的職涯?樹牧說這有現實上的難處。移民多已經四、五十歲,重返學堂自有困難,更要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負擔,經濟和經歷上都不允許。「另一個原因是,這裡意識形態很不同,在這裡做白領人工未必高過藍領。香港和中國社會強調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,但在這裡不是,做一個藍領的收入,甚至可能高過做醫生或者護士」,因此也少了增值以重返白領市場的動力。
樹牧本身也正經歷這種轉變,他坦言一定存在衝擊。儘管移民時就預計自己未必能從事自己擅長的工作,但現實與預想還是不同,「在香港是做緊一份自己很想做的、很中意的工作,來到這裡做比較基層的工作,未必會享受⋯⋯或者很多基層的工作,不太有很大意義,但要不斷去做。」當工作不能帶來成就感,他也開始反思過往香港教會強調職場呼召意義的神學,「香港整體教會很中產化,受成功神學影響,來到這裡我很感受到,以往談呼召意義,其實是因為你有選擇,但在這裡不單我,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很重複的工作,人工兌換成港幣也不過兩萬出頭,在這個情況下,談論召命已經沒有意義」。對他來說,如今能夠養活自己或者家人,已經很了不起。
心態上有落差,是否會後悔放棄香港優厚而喜愛的工作而移民英國?樹牧倒不是這樣看。他覺得無論留下或者離開,都需要適應新的環境,很難說在哪個處境下會更快樂,也無法判斷當初的選擇是否正確。「移民我損失了甚麼?也許是香港的事奉模式、人工、陪父母和家人的時間;但來這裡生活質素變好了,在香港人很容易變得物質化,我現在損失很容易擁有一些物質的狀態,那就生活得樸素點。」因為某些原因而不情願地離開香港,自然也時常會質疑自己的選擇,但對樹牧來說,當下更重要的並非判斷得失,而是在現有的實況之下,學習去適應它,或許正因為正視在英國牧會艱難的現實,他也沒有堅持香港牧會或者教會擴張的模式,談起教會的未來,他認為「轉型成為沒有傳道人的教會,才是未來教會要走的方向」,對他來說,不一定需要職場或者教牧,保持個人、家庭和靈性的健康,也可以成為好的見證。
Marcus:放下身段後,我寧願掃地吸塵
「來英國後,最受傷的是我做第二份工,在紙廠裡工作,一個後生仔『點』我去掃地,他年紀很小,用『你去掃地啦』這樣的語氣命令我,令我很受傷。你讓我搬重物可以,呼喝我都可以,但讓我去掃地我真的頂唔順。自己都叫做讀過少少書,為甚麼現在要來掃地?但現在我寧願掃地都不想搬重物,大家(反而)很喜歡掃地吸塵這類工作。放下身段真的很難,最受傷的就是要學習將身段放下。」
說起這段經歷的時候,Marcus的現職是一名貨倉工人,已經返工超過半年,一週返四天休三天,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,只有半小時放飯時間。「開始返工非常辛苦,不知道如何將貨物搬上卡板,連卡板都不會拿,很『論盡』,不懂怎麼包貨品,搞到很『論盡』,效率非常低下,整天被人投訴被人罵」;其次是從貨櫃中卸貨,「貨櫃環境很差,很黑很大塵,貨物還會摔下來,都要自己帶裝備比如電筒手套進去」。體力消耗高、工作環境危險還不算,最要命的是,這份工作要「追數」,公司有系統紀錄每個工人每天卸貨裝貨的數量是否達標,自己效率不高,更會拖累工友。

幸而貨倉有一班香港工友,不介意自己也要「追數」,願意出手耐心教Marcus,「我剛進來像個廢人一樣,做事很蠢很慢,在我最辛苦的階段,他們伸出援手教我怎麼做事,令我不被人炒」。在香港身為自由傳道、並從事音樂事工的Marcus在這過程中學會了更加謙卑,「我只會看書和寫點東西,我以為我要牧養羊群,但現在是羊群牧養我,讓我承認自己的不足,虛心面對。這份工作也教會我觀察,觀察別人面對的困難和壓迫,透過觀察別人的表情、動作和做事的方式,我學會怎樣看人,很多在香港都是看不到的。不要看低一個只會做倉工的人,我發現原來自己真的會以貌取人,都在學習不要那麼快對一個人下定論,這是我學到很深刻的東西。」
香港職場神學只是借基層人士過橋
人人都覺得英國生活環境好,空氣好、節奏慢、私人時間與工作時間分明,但Marcus卻不是這麼看,「我們這些藍領,工作環境真的很差。」貨櫃冬冷夏熱,缺乏裝備,處處都是安全隱患;做散工雖然自由,但沒有保障,隨時都可能沒工開;更雪上加霜的,是遭管理層的刁難挑刺和種族歧視。
「這裡的經理不是很喜歡我們香港人,可能因為我們語言不是很好,不太懂當地文化,但做事很勤力,但原來在這裡不是能做事就ok,還要會和他們吹水傾解,但我們不會,所以就被經理為難,當我們做到要求A,他就會提出要求B,甚至造假數字,冤枉你效率不夠。」Marcus還曾被經理要求「篤灰」其他香港人,污衊他人做錯事,但Marcus拒絕了,卻從此遭到經理針對,也正是因此,儘管他早過了試用期,可以拿到正式合約,但三個月過去仍遲遲未能拿到。Marcus和工友不是沒想過找工會維權,「但首先要收集證據,在倉裡面不能用電話錄影錄音,就很困難」。面對種種壓迫,Marcus提及最多的詞,不過是「頂硬上」。
自己有了基層的體會,Marcus才更明白基層真正想的是甚麼,因此說起香港的職場神學,不免義憤填膺,「香港的職場神學關心的都是老闆的利益,純粹借基層人士來過橋,用完就算,沒有真正關心基層的需要,將他們的困難合理化,福禍都是上主的禮物,這些禍你忍受得了嗎?」如今他體會到,身為基層人士,百分百的付出就有百分百的收穫簡直是天方夜譚,自己根本不會奢想。「我現在從沒想過自己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,我只想工作十二小時不被老闆壓迫,不被罵,然後放工,『逗份糧』。我只希望你給我一個讓我工作舒服一點高效一點的環境,有裝備,手套,不被貨物割傷,供應頭盔,不至於貨摔下來『穿頭』」,僅此而已。
用笑話抵擋謊言,萌發中的香港基層神學
身在貨倉,Marcus卻說他從未放下自己傳道人的身份,「是這個撐著我一路捱到現在」。有些人也許覺得在香港牧會很累,來到英國想休息一下,不用再過上每天24小時一週七天都在返工狀態的生活,但他並不這麼想,只是如今要轉換一種形式。「我一直有信仰反思,這份工作給我的機會是思考,現在我工作上手了,閉著眼睛都能做,就有十二個小時可以不停想,甚麼是牧會。」逐漸地他感覺自己建構出一些初步類似貨倉或者藍領神學的東西,這是從他們工作處境的實況出發,「我們做倉的,見到很多謊言在裡面,不公平,歧視我們語言不準,歧視我們的膚色,不給我們足夠裝備,做假數冤枉我們」,而他感到,能讓受壓迫的基層人士在工作場所回到真實,不被這些謊言欺騙,就是一種關心。
比如和工友一起吃飯的時候,Marcus會故意用誇張和講笑的方式,講述在工作中發生的那些被壓迫、被冤枉、被欺負的經歷,以此來嘲諷管理層和他們的不公處境。面對經理無緣無故甚至很無聊的責問,香港人通常不會反駁,只是麻木地承認是自己的錯和問題,但「長時間這樣,就不知道這些指責究竟是真是假,只是在麻醉自己」。用笑話的方式應對,Marcus將那些遭遇放大,才能看清楚這其中的謊言和不真實,才能使人回到真實中,「我見到很無理的要求,就放大成笑話,告訴大家這是一個假象,世界不是這樣的。」Marcus講述時語氣堅定而認真,充滿鬥志,幾乎讓人看見斯科特筆下的「弱者的武器」和被壓迫者的「潛隱劇本」。
Marcus仍抱著事奉的夢想,如今他在一個工廠租了一個兩、三百呎的角落,為的是讓「一班在倉庫或者工廠被老闆壓迫的人,來這裡傾偈、聚會,令他們講出內心的東西,抒發出來」。他擅長的音樂也成為服事的方式,他打算在本地一間港式茶餐廳搞一個音樂會,不唱詩歌,而是用流行歌,比如許冠傑那些反映現實生活艱苦的歌,來回應香港人在這裡遭受的壓迫。至於職場維權,Marcus也沒有放棄,「不公平對待、頂唔順真的要講出來,如何講又是一個學問」,他打算搞讀書會來討論,遇到壓迫的時候究竟該如何處理,而現在若在工作環境中不能與資方針鋒相對,至少他的事工是一個可以發洩的渠道。
中大音樂系畢業,受呼召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讀神學,Marcus是帶著牧會的心態來到英國,遭遇如此自然也曾有過很大的衝擊,「我知道不可能做文職,但沒想過會那麼惡劣」,也曾對信仰產生懷疑。但體驗過基層的艱難,更試過一齊同行,心態發生變化。如今做基層、能否拿到正式合約,他都已經不再在乎,重要的是他的基層事工,「我用了很多時間成本做出來,希望可以發揮自己的效用」,看到前路,更有一班同行者,「雖然工作還是那麼辛苦,但放工還是開心的」。






你必須登入才能發表留言。